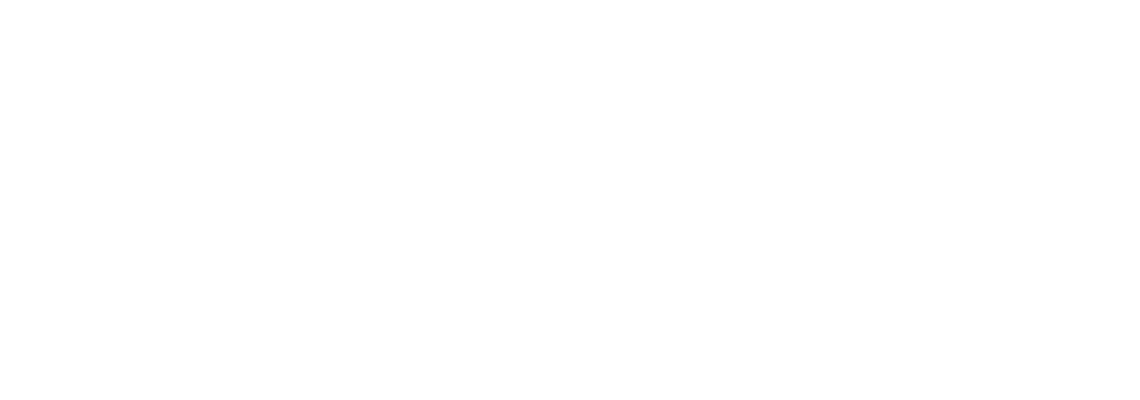生育支持政策的系统性重塑:挑战与应对
日期:2024-05-06 05:46 | 人气:
贺丹 史毅
[摘要] 少子化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未来发展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对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产生重要影响。从多个维度讨论现阶段实施生育支持的重要意义,分析对现有生育配套政策进行系统性重塑存在的困难与挑战,研究发现,核心基本制度缺位是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面临的最大挑战,在政策设计中应优先解决主要矛盾,避免陷入制度惯性、福利主义、效益悖反、政策失衡等陷阱误区。既要及时转变政策理念,持续强化高位推动,重塑政策框架,建立以生育保险、婴幼儿照护和生殖健康为核心的三项基本制度;也应明确政策责任主体,做好长期投入准备,细化配套支持措施,完善政策效果追踪和评价机制。
[关键词] 生育支持;家庭发展;人口战略;政策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3)02-0004-08
近年来,持续下降的生育水平引起我国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少子化问题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为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不容忽视。为积极适应人口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和新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人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强调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将生育支持问题提升至重要地位。全面认识我国应对低生育率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系统分析当前生育配套政策的群众需求和问题局限,深刻理解新时代生育支持的概念内涵和核心价值,是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基本前提,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应有之义。
一、充分认识生育支持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第一,生育支持是一个长期性问题,人口零增长区间是做好政策储备的关键时期。在过去10年中,我国为适应人口转变特征及时调整了生育政策,先后实施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政策调整对家庭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上升产生了一定影响,[1][2][3][4]但出生人口下降的形势依然严峻。2017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从1786万降低至956万,2022年人口增长由正转负,总量减少85万,① 人口拐点的出现比以往研究预期提前了5年。值得注意的是,人口拐点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完全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而是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出现波动性变化。当人口自然增长在零值上下变动时,可以认为人口进入了零增长区间,这一阶段可能延续5年甚至更长时间。日韩等多国经验显示,人口负增长后再出台相应对策措施则为时已晚,在生育水平下降的过程中如果长期采取不干预政策,错过政策变革的最佳时期,生育率将长期处于低迷状态,需要更大、更长期的投入才能缓慢回升。在人口零增长区间内,把握时机迅速建立起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及时扭转出生人口下降趋势,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是我国需做出的战略选择。
第二,生育支持是一个共识性问题,加大相关政策投入是多数发达国家的共同做法。积极应对低生育水平不是我国面临的独有问题,而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转变进入一定阶段的普遍性结果。[5][6]在过去的45年中,低生育水平问题也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世界上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国家比例从14%上升至52%,低于1.5的国家比例从1%上升至20%,认为本国生育水平太低的国家比例从9%上升至28%,已有55个国家开始出台一系列以提高生育水平为导向的社会政策,[7]大多数国家将低生育水平与人口减少、老龄化和可持续性发展联系在一起,提高生育率已经成为多数发达国家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尽管许多国家并未将相关政策定义为生育支持政策并形成体系,但这些措施实际上发挥着支持家庭生育、促进生育水平回升的功能和效果。
第三,生育支持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单一部门或政策措施往往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生育支持是一项综合性社会工程,涉及部门较多,覆盖范围广,影响因素复杂,需要综合应对。在已有研究中,生育水平下降主要被归于四类因素:一是文化因素,主要来自性、婚姻、家庭观念的快速变化;[8]二是经济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生育养育带来的机会和经济成本增加等;[9]三是社会因素,如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工作场所条件和儿童保育服务的可及性;[10]四是生物因素,如不孕不育、性与生殖健康水平等。[11]上述因素并非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形成了一系列更广泛的环境条件,影响个人和家庭的生育计划及其实现能力。因此,生育支持不是通过单一的政策措施为家庭生育提供支持,而是从时间、经济、服务等不同维度为家庭生育提供保障。
第四,生育支持是一个民生性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民获得感是核心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生育并非单一、独立、短期的行为或事件,而是与养育、教育、就业、住房、养老等一系列民生问题密切关联的长期过程,对一个家庭内不同成员的职业发展、经济状况、时间分配和生活质量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生育水平下降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家庭婚育文化观念变化、育龄人口规模减少、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上升、平均婚育年龄推迟、新冠疫情冲击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水平进一步降低,[12][13][14][15]如何通过综合性社会政策保持和提升生育水平变得愈发迫切。如果民生系列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善或解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就难以提升,生育意愿和水平就难以回升。积极应对低生育水平,不仅是保持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的发展问题,更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家庭和谐关系、提升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民生问题。
第五,生育支持是一个发展性问题,有助于强化人才在国家竞争力中的支柱性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人才是第一资源”,要“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未来大国博弈,是高龄少子化背景下的竞争,人口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人口素质和劳动参与两方面。首先,生育支持对儿童成长和早期发展影响深远,对于国家整体人口素质提升、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是提升人力资本总量、强化国家人才储备的基础性工程,关系到我国第二个百年计划的人力资本水平。其次,生育支持对释放潜在人才供给具有积极作用。既可以将高素质人才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扩大劳动参与;也可以减轻家庭养育压力,改善工作和学习效率,提升专业技能水平。
第六,生育支持是一个安全性问题,是防范和化解人口安全风险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高到统领全局的战略高度。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变量,人口安全是新兴安全领域重要内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国人口发展风险挑战也在经历着重大的转换,人口安全风险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延伸。人口安全风险诱因从表层显性因素转向深层隐性因素;风险发生机制从单向因果传导转向复杂系统传导;风险发生场域从实体领域延伸至非实体领域。积极应对低生育水平,有效防范和化解人口风险,是新时代人口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现有生育配套政策需要系统性重塑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国已经围绕生育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和支持措施,但这些措施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人口发展战略需求,难以解决当前群众急难愁盼的“生不起”“养不好”“生不出”等现实问题。生育保险制度覆盖率低、婴幼儿照护服务投入少、辅助生殖服务支持存在空白,核心支持制度缺位、政策实施效果不足等较为突出的问题成为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这对系统性重塑生育配套政策措施提供了更高要求。
第一,传统生育服务保障理念难以适应人口发展战略转型需求。在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要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时期,我国围绕生育问题建立了一系列的保障和服务政策,核心内容包括产假制度、生育保险、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等。在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我国生育保障制度也需要基于现实问题作出相应调整,生育服务保障政策的目标、内容和形式也应发生重大变化。2015年,我国政府提出“生育支持”的初步构想,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中提出要“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病残照料等在内的家庭发展政策”,这是中央文件内第一次出现“生育支持”的概念,但在该阶段生育支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要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并将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作为主要目标纳入顶层设计。其后,2022年,国家卫健委等十七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从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多个方面,提出一揽子支持政策,为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措施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尽管不同层面的生育支持政策已有雏形,但缺乏清晰的制度设计,各地具体生育支持措施的制定也仍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既缺乏系统性的政策汇总和梳理,也缺乏相应的政策效果评估。
第二,现有职工生育保险制度难以有效保障女性生育经济和职业发展损失。自1994年《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出台以来,职工生育保险作为生育保障的核心政策内容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保障范围、标准、方式现今已难以适应和满足新的发展需求。首先,生育保险制度覆盖范围较窄。覆盖对象仅针对正规就业的劳动者,难以覆盖未就业和非正规就业者的普通居民。截至2021年底,全国参加生育保险仅为2.39亿人,享受生育医疗待遇和生育津贴待遇的女性远低于当年实际发生生育行为的妇女规模。其次,生育保险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碎片化。不同人群、地区之间的保障待遇差别较大。特别是在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合并之后,多数地区因为医保支出增长过快、筹资水平不足、生育津贴占比较高等问题难以提高生育保险待遇。部分地区对产前检查和分娩实行限额支付,报销费用远低于实际花费;部分地区则实施100%报销政策,少数地区还发放生育医疗补贴,导致不同地区的生育保障水平悬殊,影响制度公平性。最后,生育保险与产假制度的衔接性不足。我国的生育保险同时包含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费用,生育政策调整过程中各地纷纷将产假延长,但延长期间的生育津贴发放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导致新的产假政策有名无实、难以落地。
第三,婴幼儿照护服务投入难以有效解决“没人带”的难题。婴幼儿照护服务是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2019年以来国家将普惠托育服务作为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的发展重心,托位数量迅速增加,但其服务模式、价格和内容仍难以有效满足广大家庭需求。首先,婴幼儿照护服务覆盖人群有限。按照我国托育服务的发展目标,“十四五”末完成建设的托位数仅能为20%左右的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服务,仍有接近80%的家庭需要其他形式的照护服务支持。其次,婴幼儿照护服务价格较高。中央及地方对托位总量有规划目标,但对备案、普惠、公办托位数量和比例缺乏明确发展要求,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有效服务供给不足,多数托育服务价格高于居民消费能力。再次,普惠托育服务缺少常态化财政经费支持。各地补贴措施投入力度小、出台时间晚、执行期限短、覆盖范围窄,难以有效降低托育服务成本和价格。最后,婴幼儿照护服务城乡均衡性不足。当前我国婴幼儿照护服务主要聚焦于发展城市地区托育服务,对农村地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涉及和投入有限。
第四,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保障难以有效解决“生不出”的难题。关于我国不孕不育率和辅助生殖需求的估计,目前存在多种数据来源,但均反映出不孕不育率上升及所带来的辅助生殖需求上升的趋势。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按照15.5%的不孕率估计,我国约有3671.7万对夫妇受到不孕症困扰。① 尽管我国辅助生殖机构配置数量和技术类别非常丰富,技术条件也已经达到较先进的水平,但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仍然存在一定阻碍,在具体应用过程中也面临许多困难和困惑。目前,不孕不育检查和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费用成本较高,但不在医保政策范围之内,相关费用均由家庭自行承担,经济成本影响了很多家庭辅助生殖服务的可及性。伴随我国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初婚初育年龄推迟、大龄未婚比例上升等趋势凸显,未来的辅助生育需求将进一步提升。
三、警惕生育支持政策设计的四大陷阱
在对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系统性重塑的过程中,要特别预防把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持久战当作快打快收的攻坚战,只注重单项政策效应而忽视激励相容的顶层制度设计,要注重引入系统观念,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配套措施组成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方向精准、形式丰富的政策支持体系,避免陷入制度惯性、福利主义、效益悖反、政策失衡等陷阱误区。
第一,警惕制度惯性陷阱。当前,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设计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有政策的路径依赖,难以打破传统制度框架,政策创新缺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为主要的体现是将生育支持的重心局限于对妇幼保健、生育保险、生育假期等与生育直接相关的政策优化,而忽视了生殖健康、婚恋服务、婴幼儿照护、养老照护、住房保障、文化宣传等与生育间接相关的政策投入。二是照搬照抄发达国家政策经验,忽视本国婚育文化特点。世界上没有最好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只有最适合本国国情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优化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既有各国共有的问题,也有本国特有的问题。欧美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是在其政治环境、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设计并实施的,并不完全适合东亚儒家文化中应为子女终生负责、结婚是生育的前提等价值观念。对中国的问题,只能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法解决,完全照搬照抄国外的制度政策和经验做法,可能会效果甚微,甚至出现适得其反的情况。
第二,警惕福利主义陷阱。生育支持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持续的政策、资金、人力资源投入,因此生育支持政策设计要考虑政策实施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避免陷入福利主义陷阱。一是做好长期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在经济增速趋缓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平稳可持续增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支出端面临各项增支需求,中长期收支平衡矛盾突出。应建立基本财政投入制度,持续优化支出结构、统筹整合存量资金,保障生育支持政策的连续投入。二是做好服务规模变化的制度安排。伴随生育支持政策措施的出台,生育水平可能出现波动性增长或持续回升态势。无论是出生人口数量出现何种形式和方向的变化,都将相应地引起生育支持政策资金投入的变化。充分考虑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应,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适时调整资源分配策略,避免出现生育支持政策效果明显但财政投入准备不足的情况。
第三,警惕效益悖反陷阱。生育支持领域内不同措施的目标、功能和作用并非完全一致,有时会表现出损益关系,某一措施的强化可能会引起其他措施的弱化,最终影响整个政策体系作用的发挥。首先,生育支持不是“福利竞赛”,应做好精准施策,避免出现政策目标与对象不一致的情况。应基于生育意愿低的关键原因与关键人群进行政策设计,对子女数量不同的家庭予以不同程度的支持,针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提供差异化的经济补贴。如果对所有家庭实施完全统一的支持标准,那么这些措施很可能会分散有限的财政资源,减弱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激起新一轮的地方性人口福利竞赛,加剧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失,反而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其次,生育支持不是“无源之水”,应避免出现将政策成本转嫁给企业或家庭的情况,加剧雇主惩罚现象。当前多数政策对经费来源、组织保障缺少明确的表述。比如在延长假期的相关政策中,有些省份没有明确规定新增假期工资与津贴的资金来源,如果假期的工资由企业支付,那么企业会想办法转嫁成本,不招或少招女性,进一步加剧对女性的就业歧视。产假时间越长,雇主所要承担的用工成本越高,女性重返职场的障碍越大,就业困境愈发突出,反而产生与政策预期目标完全相反的效果。
第四,警惕政策失衡陷阱。在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过程中,要重视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体现家庭在生育中的主体地位,特别要考虑城乡、人群和区域差异问题。首先,避免出现“重城市,轻农村”的制度安排,提高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城乡公平性。由于财政能力的差异,不同地区生育支持力度有强有弱,应加大向薄弱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进生育支持政策财政投入和服务资源配置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其次,避免出现“重户籍,轻流动”的制度安排,将生育支持政策与户籍脱钩,建立以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为主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高生育支持政策的便利性和可及性,保障流动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生育支持政策。最后,避免出现“谁受益,谁投入”的制度安排,加强生育支持政策的区域统筹,分担欠发达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成本,做好服务设施配置、人员配备的衔接。充分考虑区域发展特点,重视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之间、人口密集和人口分散地区之间的差异,在财政转移支付的过程中有所侧重。
四、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路径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人口发展的重大转折期,也是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关键时期。我国的生育支持政策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相对完整的、综合性的政策体系。因为各类政策的实施力度、执行程度和落实难度各不相同,政策之间的协调性、相关性和整合性也不尽如人意,政策部门化、碎片化问题比较突出,缺乏顶层设计和规范标准,基层落实缺乏政策规范依据,未能形成合力,存在综合效应不明显、实效性不强、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因此,现阶段尽快构建起一个整体性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显得更加重要。应优先解决主要矛盾,从政策理念转变入手,强化高位推动,重塑政策框架,构建基本制度,融入系统观念,保障政策投入的可持续性,推动部门协同和政策落实,逐步提升政策的公平性和包容性。
第一,转变政策理念,高位持续推动。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和发展的事业。由于我国长期实行控制生育的政策,要转为支持生育最关键的是要转变理念,将生育支持作为国家战略,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核心要义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内部理念引导和外部政策支持减轻育儿焦虑、教育焦虑、社会流动焦虑,促进个人婚姻和生育愿望的实现,保障家庭选择生育数量和获得生育服务的权利和能力。同时,应避免将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混为一谈,需要强化顶层倡导和组织领导,在党中央、国务院层面成立专门的少子化应对协调议事机构,设置相对独立的生育支持职能部门,明确战略目标和阶段任务,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指导和督促各级各部门实施强有力的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见效。
第二,重塑政策框架,建立三项制度。生育友好社会生态的形成离不开基本制度的构建,现有碎片化的政策不足以支撑基本制度的构建。当务之急是要重塑框架,明确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基本制度和配套措施,围绕“没人带”“养不起”“生不出”等突出问题建立三项基本制度,强化生育保险、婴幼儿照护服务和生殖健康服务的核心功能作用,并将其作为未来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三大支柱。一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生育保险制度。将生育保险覆盖范围从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拓展至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提升生育保险制度的公平性。构建所有居民生育津贴制度。建立由财政支持、资金来源多元化的社会福利性质的城乡居民生育津贴、育儿假薪酬、育儿补贴制度。二是建立兼顾供需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制度。将家庭享受育儿服务上升为法定权利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水平和责任分担机制。采用“补供方”和“补需方”相结合、“补砖头”和“补人头”相结合的方式,既向托育机构的建设和运营提供资金支持,保障城乡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的稳定可持续发展,也为困难家庭额外发放育儿津贴或育儿券,保障重点人群的基本服务需求。三是建立全过程保障的生殖健康服务制度。将辅助生殖检查、治疗和手术费用纳入医保,向经济困难或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提供一次性补贴。在各地按标准配置辅助生殖设施设备的基础上,加大中西部地区、地市级辅助生殖机构的资源投入,提高服务资源的均衡性、公平性、可获性和可及性。
第三,明确责任主体,长期稳定投入。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目标对于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是生育水平提升的重要受益者。在生育支持方面,国家作为受益者应承担必要和基本责任,但不是无限地承担所有生育成本。在财政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要量力而行,要考虑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和可持续性。财政投入可以低水平起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应增加,但必须要有制度性突破,形成常态化的基本财政投入机制。分散化、片段式的财政投入不仅会导致各类政策难以形成合力,而且可能会影响全社会对于公共政策的信心,对改善生育意愿起到相反作用。
第四,宏观政策配套,完善政策评价。婚育选择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稳定就业、家庭收入、教育负担等是最重要的长期性影响因素,这些宏观经济社会政策的改革应当与支持生育的政策导向一致,单独的生育相关的政策措施无法对生育率提升起到决定性作用。与生育支持紧密相关的政策也要与相关领域改革衔接配套,保持统一性和协调性,综合实施现金补贴、税收减免、育儿假等政策,多方面降低家庭生育养育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因此,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不应局限于生育本身,而是在三项制度的基础上围绕家庭发展打出政策组合拳。同时,应基于人口统计、行政登记和社会调查等多来源数据,定期开展生育政策实施效果追踪评估,对政策措施的完整性、包容性和公平性进行综合评价,缩小政策支持力度的区域、城乡和性别差异。从个体和家庭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视角评估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建设和实施效果,推动各类政策资源的统筹整合与规划,从婚前检查、优生优育服务、生育假期、婴幼儿照护、健康教育、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不同方面为家庭发展提供服务,促进妇幼保健、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养老医疗等不同类型服务的无缝衔接,打造完整生育支持服务链条。
[ 参 考 文 献 ]
[1]张晓青, 黄彩虹, 张强,等. “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J]. 人口研究, 2016(01).
[2]贺丹, 张许颖, 庄亚儿,等. 2006~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J]. 人口研究, 2018(06).
[3]石智雷, 吕婕. 全面二孩政策与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变动[J]. 人口研究, 2021(02).
[4]Kane D, Li K. Fertility cultures and childbearing desire after the Two-Child Policy: evidence from southwest China[J]. 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 2021: 1-19.
[5]郑真真.生育意愿研究及其现实意义——兼以江苏调查为例[J].学海,2011(02).
[6]Poston, D. L. . Low Fertility Regimes and Demographic and Societal Change. Cham: Springer, 2018. pp. 15-36.
[7]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 2021: Policies related to fertility. UN DESA/POP/2021/TR/NO.1.
[8]Sobotka T. Post-transitional fertility: the role of childbearing postponement in fuelling the shift to low and unstable fertility levels[J].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2017(S1).
[9]Matysiak A, Sobotka T, Vignoli D.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fertility in Europe: A sub-national analysi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21(01).
[10]Miettinen A, Lainiala L, Rotkirch A. Women’s housework decreases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 among Finnish couples[J]. Acta Sociologica, 2015(02).
[11]Kim N, Kim C J. Two Attempts to Medicalize Reproduc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J]. Asia Pacific J. Health L. & Ethics, 2017(11).
[12]贾志科, 风笑天. 城市青年的婚恋年龄期望及影响因素——以南京、保定调查为例[J]. 人口学刊, 2018(02).
[13]葛玉好, 张雪梅. 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J]. 人口研究, 2019(01).
[14]翟振武, 刘雯莉. 中国人真的都不结婚了吗——从队列的视角看中国人的结婚和不婚[J]. 探索与争鸣, 2020(02).
[15]张翠玲, 李月, 杨文庄,等.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出生人口变动的影响[J]. 人口研究, 2021(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源大数据人口监测的理论逻辑和技术应用研究及示范数据库与决策平台建设”(22&ZD197) 。
[作者简介] 贺丹,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史毅(通讯作者),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①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2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再上新台阶[N]. 2023-1-17.
①资料来源:王晖、龚双燕、史毅. 开展辅助生殖支持专项试点,应对低生育率下生育模式变化[N].人口决策参考,2022(142).